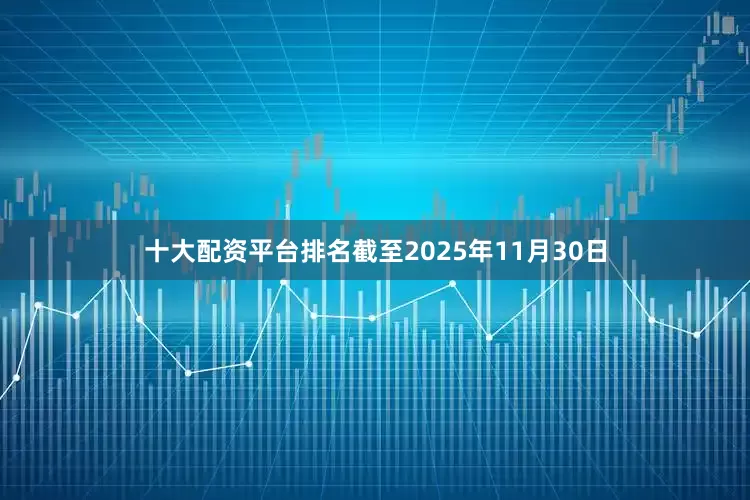当徐倩老师谈到“虚幻憧憬”时,我想到两部小说。
一部是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,一部是毛姆的《面纱》。爱玛.包法利婚后立刻陷入对现实的不满中,不满于生活的庸俗无趣,不满丈夫的迟钝与平庸。而《面纱》中的凯蒂也同样不满意丈夫带给自己的生活现状,以及不满意丈夫的平庸和无趣。两位女性都向往着充满浪漫激情的爱情以及金碧辉煌的生活。她们都出轨了自己的丈夫,与看似理想的男人发生婚外情,她们都渴望着理想中的爱人来救赎自己。
她们憧憬的与其说是某个具体的人,不如说是爱情本身所能带来的那种戏剧性的、能将自己从平庸中拯救出来的感觉。遗憾的是她们的情人都弃她们如敝履。

截然相反的,是两位女性最终的结局。爱玛呈现了活在想象和虚妄憧憬中的人所能走向的某种极端——为了维持虚假奢华而债台高筑,最终服毒身亡。而凯蒂,亲临了可怕的霍乱发生地,经历了丈夫的死亡,在绝境里重新寻找真实的自己和属于自己的意义。她重新认识了丈夫,看到了无趣、平庸背后丈夫的光芒,也借助情人的抛弃最终看清了自己可笑的幻想。曾经的凯蒂死了,一个新生的凯蒂决定扬帆起航,去面对真实的自己与真实的生活。
故事总是令人唏嘘,开启上帝视角的读者总能轻易为爱玛和凯蒂做出正确的选择,但身处故事中的人,为什么会深陷虚幻憧憬无法自拔?为什么触碰真实是那么不易,甚至要经历一场“向死而生”的旅途?

“爱而不得”的创伤
9月14日,徐倩老师在深圳的观影沙龙中,有两位朋友对徐倩老师说:“我好喜欢你,但是我好像只能远远地看着你,我也觉得看着你就很好了,来跟你打招呼我很紧张。”
这似乎在说,喜欢一个人的同时,觉得自己不能与对方走得太近,好像自己喜欢的人是不会喜欢自己的,不会在意自己,自己是会被拒绝的,又或者说自己喜欢的人,是可望而不可及的。很多女孩也会这样对待自己,找一个自己并不真正喜欢的人做恋人,真正喜欢的人像天边一轮皎月,是自己触摸不到的。

徐倩老师说,这种“喜欢但得不到”是一种创伤的感觉。这种感觉,描述着两种信念。
一种是:我爱的人,往往是不在我身边的。如果我喜欢一个人,我也会跟他保持距离,这很可能是在重复早年对重要他人强烈的依赖,但这个人不在身边、无法被依赖的处境。早年曾经历过长久与父母分离,或者与主要照料人分离,并且没能得到很好养育的人,成年后很可能就会处在这种感受里。他们也会让自己所爱的人,与自己保持距离,因为曾经自己爱的人就不在身边,于是重复为自己制造爱而不得的熟悉感。
另一种是:我爱的人不爱我,他们离开是因为不爱我,不在意我。这是在说,自己无法得到渴望和期待的人,是因为重要的人心里没有自己,他们有更重要的事,自己是被忽视的,是可以被留下抛在一边的。有时,这的确是现实,比如父母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,需要离开孩子去外地;又或者要忙着带弟弟,把女儿交给其他人照料。而在现实之外,这种”他们不爱我才不在身边“的想法也来源于自恋,自恋性地认为是自己的原因,才使父母抛下自己。
这种所爱之人不在身边,被重要他人抛下的处境,会制造创伤的想法,认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没有人爱自己,所以自己爱的人不爱自己。
徐倩老师提了一个问题:“我们设想一下,如果自己是一、两岁的小孩,父母离开了我们,我们不得不跟着亲戚过活,同时认为是自己不够好才被父母抛下,在这样的处境里,我们要怎样才能存活下来?”
我们会讨好,会学会看别人脸色,会知道要讨别人欢心,才能在寄人篱下的处境里给自己找一个安住的角落。这是我们能使用的一种现实策略,同时,我们很可能还会使用一种幻想策略,在想象里,自己不在身边的父母是完美的,是非常爱自己的,是理想的好父母,有很多资源、很多能力,并且幻想着他们会在某一天来接自己回家。
想象里的家十分美好,住在温暖、明亮的大房子里,父母视自己如珍宝。曾有幼时寄住亲戚家经历的朋友说,每当父母偶尔来看自己时,都是自己最幸福的时光,父母那么温柔,对自己嘘寒问暖,会带好吃的来,会对自己特别好。那时以为父母就是如此令人憧憬的。后来被接回家后,仿佛从幻想走入现实,真实的家里一地鸡毛、满目硝烟,父母之间冲突不断,对待自己的态度也变得懒散、随意、漫不经心,甚至还会横眉冷对、百般挑剔。

困难的地方在于,此前的幻想和某种局部展示构成的假象,与真实反差过于巨大,使人难以接受真实的模样,也难以放下曾经美好的幻想,这是一种十分割裂的感受。这种美好想象与残酷现实的切割,来源于一种名为“分裂”的防御机制。
分裂会使我们看待事物时,简单粗暴地将其分为好与坏的绝对对立。早年间,这种防御非常重要,能帮助孩子在心里保存好妈妈的安稳感受,让自己能在心里建构安稳的根基。但如果我们早年所处的环境过于糟糕,这种分裂也会被推向极端,变成过度美好的幻想与极其糟糕的现实的对立。这两个部分之间分裂得越彻底,越对立,打破幻想接触真实的阻碍就会越大,因为这其间的落差实在太巨大,令人无法承受。这种分裂,很可能会延续至成年,哪怕所处的环境不再糟糕,但依然会蜷缩在幻想里,使用分裂的防御机制抵抗现实。
徐倩老师谈到,很多时候我们越是幻想一种遥不可及的美好,就越是在打压真实的自己。我们要看到自己憧憬的美好背后,可能隐藏对自己的暴力,那是在说:现实的你很糟糕,你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,很多要求没有达到。也就是说,内在那个不被自己喜欢的自己,也许从没被自己真正看过,我们只是学着父母或其他重要他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。当我们不被重要的人喜欢时,我们也变得不喜欢自己,而内在那个真实自我的模样,其实从未被真正看见。在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和意愿去看内心的自己时,也许会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堪和丑陋。
当然,这个过程会很不容易,会需要从幻想里出来走进真实里看一看,会触及很多原始的恐惧和焦虑。如果有意愿也有条件,给自己找一位咨询师做做精神分析,能使这个过程变得安全、可控一些。同时,这个过程也许会让我们找到某种途径,让真实的自我绽放,焕发出由内而外的自信与活力。

现场访谈:依赖与独立
在现实生活中,“想象”常常在扮演重要角色。很多时候也许我们不是在和真实的人相处,而是在和想象中的对方相处,有时想象、自我脑补的部分过于自然,无法被觉察到,这会遮蔽我们去看真实关系的细节。关系,也可以被看作投射游戏,而完成投射过程的重要帮手,就是我们的想象。
第一位现场连麦的访谈对象,带来了自己与婆婆相处困难的议题。婆婆因为某些原因住进了小夫妻的家,即使访谈对象拒绝,婆婆还是住了进来,因为丈夫很需要婆婆提供的照顾。婆婆无微不至地照顾,让丈夫在访谈对象心里变成了婴儿。
了解了前因后果后,徐倩老师谈到婆婆的照顾里有入侵的部分,以及婆婆的存在使访谈对象被排除在外。徐倩老师还做了更进一步的诠释:“你与婆婆的关系问题里,有一部分很可能是与老公的关系问题。即使你拒绝,婆婆还是住进来了,你愤怒表示要走,老公无动于衷,好像你与老公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。”
访谈对象认为是婆婆的出现,使自己与老公的关系有了变化,但在进一步谈论中,对老公的愤怒逐渐显现。在愤怒的另一边,是对老公的依赖,同时也有对自己独立的渴望。访谈对象认为如果自己独立了,就能够离开婆婆和老公,可以不再依赖其他人而活了。

徐倩老师回应了一个很重要的解释:
“你觉得独立就是要跟老公分开,但也许不是这样的,跟老公分开不一定就是独立,而跟老公在一起也不一定就是依赖。独立与依赖,看的是你内在的婴儿与你内在父母之间的关系。换句话说,在你心里有一个婴儿,是很想依赖妈妈的,这个妈妈就是现实中的老公。而你的一些情绪和需要在和妈妈的关系里是被忽略的,这让你很委屈、愤怒,所以想要离开。但这个离开,是一种行动化的反应,它在说你感受到被忽视了。因此其实你在跟老公的关系里,是觉得内在婴儿没有被照顾好的。
这也是为什么你感到与婆婆之间是三角竞争,老公被婆婆抢走了,你就没有妈妈了。所以,你需要的也许是更多看看自己内在受伤的、被排除在外的婴儿。”
访谈结束后,徐倩老师谈到很多时候我们会避重就轻,这也是在防御。看似是与婆婆的问题,但其实核心是与老公的关系问题。而在访谈对象与老公的关系里,其实呈现的是内在婴儿想要依赖妈妈,但被妈妈忽视的议题。访谈对象想要分开的冲动里是有恐惧的,但又觉得要真正长大独立就需要分开,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去看看内在受伤婴儿的需要。
我们可以看到幻想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,也许在幻想里,婆婆是制造问题的人,处理了与婆婆的关系就能解决问题,但其实这层幻想遮蔽了真正的问题,让我们不用去看自己内在的婴儿正在发出怎样的声音。另外,也许在与老公的相处里,在潜意识里把老公幻想成能照顾和满足自己的好妈妈,婆婆的进入,其实某种层面戳破了这层幻想,使原先隐蔽的问题暴露了出来,也使访谈对象被破处在问题中,不得不来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第二位访谈对象,也同样谈到了与幻想有关的议题。因为父母关系的动荡、争吵,对自己的冷漠和伤害,访谈对象更倾向于待在自己的幻想里,很多人都反馈过访谈对象像是活在自己世界的人。现在访谈对象有一部分想要从幻想中出来,但还有一部分在抗拒从幻想中出来。徐倩老师谈到,两位访谈对象似乎都在强迫自己做自己做不到的事,这并不是改变的方向,而是强迫性重复。
无论强迫自己从幻想走出来,还是想要决绝地离开老公,其实都是在说现在的自己很不好,现在的自己走不出来还沉浸在幻想里,是很糟糕的自己。这种看待自己的视角,这种潜意识对真实自己不满,幻想着一个更好的自己的动力是需要被意识到的。这不是一种真正的走出来,这依然是一种对自己的暴力。
我再次想到《面纱》里的凯蒂,她被自己亲手制造的幻境推到绝境:远离自己的家人,母亲去世,被自己嫌弃但成为自己最后避风港的丈夫也去世了,她被抛在霍乱爆发的地带,与修女们一起照顾无家可归的孤儿们。她看见那些虚构的憧憬犹如一层层面纱被撕开,露出真实生活残酷的模样,她不得不去看自己内心的恐惧,不得不去聆听内在婴儿的声音。最终她意识到自己憧憬的金碧辉煌的生活是其他人给她套上的滤镜,她始终走在他人期待的路径上,追逐的是满足母亲的期待、超越妹妹成为更优秀的存在。
这一切使她发现,向内去看那个真实的自己空空如也,没有目标,没有方向,也没有意义。凯蒂仿佛抵达了精神层面的绝境,也抵达了徐倩老师多次谈到的“深渊”。最后,凯蒂在修道院里找到了存在的意义,接纳了真实的自我,凝聚出力量,回到父亲身边决定与父亲一起踏实生活。小说结尾时,凯蒂发现自己怀孕了,虽然不知道生父究竟是谁,但这并不重要了,她说:
“我希望她是个女孩,我想把她养大。当我回顾自己曾经是个什么样的女孩时,我深感悔恨,但已无能为力。我要把女儿培养成一个自由且自立的人。我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来,爱她,养育她,不是为了让她将来和某个男人睡觉,从而依附于他。我希望她是个无畏、坦率的人,是个自制的人,我希望她像一个自由的人那样生活。”

正如徐倩老师谈到的,独立并不表现在行为的决绝上,而是我们越多地看见内在的婴儿,越多处理内在婴儿的需要和声音,这个小婴儿自然而然就会长大。这时等我们积攒了足够的力量和底气,想离开时自然就能离开了,不再受依赖和恐惧的牵绊。
直接点击下方小程序
开始预约心理咨询

BREAK AWAY
01
02
03
人人顺配资-人人顺配资官网-专业配资公司-广东配资炒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